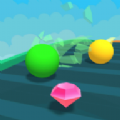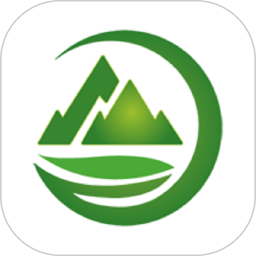《我爱你!在发布之前,导演闫涵接受了记者新闻的专访,谈了自己目前对老年群体的观察,以及长期以来对创作和人生价值的思考。

老人谈恋爱不问未来。
澎湃新闻:在过去,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年轻人是爱情的主题。老年人的爱情有什么特点和质地?
闫涵:老年人的爱和年轻人的不同。年轻人的爱情往往关乎未来。他们将来会结婚生子,有各种新的可能。但其实老年人最怕谈未来。他们在一起更多的是聊过去,有过什么经历,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他们可能没有勇气谈论未来。
但也许这也是我的疑惑之一。也许有一天当我老了,我会对未来如此恐惧吗?所以我拍了这部电影作为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。问我,老年人的爱和年轻人的爱有什么区别?在我看来,也许最大的不同是,老年人在谈爱情的时候,其实已经超越了爱情本身。更像是在爱情中混合了陪伴、亲情、友情,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。
澎湃新闻:片中两对风格迥异、境遇各异的老年CP如何对应你的观察和表达?
闫涵:这两对CP反映了我们在现实中经常遇到的两种恋爱情况。希望其中一个白头偕老,有正常的婚恋状况;而另一对其实承载了我对爱情的一些思考和探索。两个人都失去了另一半。年近六旬的他们,并不是完全孤独,对爱情和生活没有信心。所以当它们碰撞的时候,我试图去探索这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新的启示:会不会有一天当我们进入衰老的状态,心中的爱会被抹去?
澎湃新闻:电影除了谈恋爱,还讲了一些老年人在社会和家庭中面临的处境和问题。在这方面,你对老人问题有什么观察和感受?
闫涵:通过一些媒体报道,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,我们也确实知道有很多真实的情况。甚至我产生做老人题材的想法,是因为我观察了一些老人在生活中与我擦肩而过的状态和瞬间。可能我真的决定拍我爱你!这部电影可能就这两年,但这些老人的形象其实已经在我脑海里酝酿了很多年。
小小年纪就通过点点滴滴积累了对这些人物的感情。我积累的材料中,无论是新闻报道中,还是我的生活中,都包含了大量与空巢老人相关的内容。我通过整个社会的方式为我编织了这四个老人的形象,我把他们放到一个像这样的故事里来讲述,所以这部电影也包括了这些社会现实中经常出现的养老问题。
澎湃新闻:电影中有一个非常“揪心”的吃饭场景,甚至直接导致了影片中的悲剧。但是好像这些孩子自己的生活也很累。对于这样的家庭生活,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和体会?
闫涵:首先,我认为这部电影最大的意义在于它似乎在提醒我们,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。我以前从来没想过我是一个会无视老人的人。后来发现身边的人都是这样的。我们总觉得自己很孝顺,对老人足够关心。本来我也觉得自己在同龄人中做得很好。但是我拍我爱你的时候!我意识到我们认为足够的东西是不够的。
身边的老人不跟我们提要求。中国的父母太善良了,他们常常默默承受这一切。在拍这部片子的时候,我们的录音师看完片子,突然想起来他已经一个星期没有给爸爸打电话了。如果他没有看过这部电影,他可能会觉得自己两天前刚演过。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忙起来,就会忽略它们。特别希望这部电影能提醒大家对身边老人的关心。
上帝为我选择了这四个角色。
澎湃新闻:四位主演的选角流程是怎样的?
闫涵:其实我在写剧本的时候,先有了李慧如的形象,也就是惠英红老师,还有梁家辉老师演的谢鼎山的形象。在接触了两位老师后,我根据她们的形象,思考能和她们的另一半匹配的角色。实际上,叶童先生是辉哥先生推荐的。翻了翻两位老师的一些资料和视频,觉得很对。这次选角完全出乎我的意料。
至于大鸿倪先生,我隐隐约约感觉他很适合常伟杰这个角色,但我根本不了解他,也没见过他。后来他第一遍就看了,第二天就见了我。聊了两个多小时,我确定他就是那个角色。好像整个选角过程都不是我选的,但好像是老天在给我选这四个角色。
澎湃新闻:四位老师的合作是如何产生一点化学反应的?
闫涵:辉哥和叶童先生是多年的同事,很快就会有默契和火花。大洪小姐和惠英红小姐并不是那么熟悉,而大洪小姐的内心是非常敏感细腻的,只是她不太喜欢表现自己,所以他们两个才会慢慢来。
在打开电脑之前,我们花了十多天的时间排练,让几个老艺术家互相熟悉,有默契。随着排练的进行,四位老师无论是彼此之间的友谊,还是情感的专注和默契都有所提升。
澎湃新闻:几年前,市场上有一种声音说,老年演员只能演配角。你的意思是给他们创造一个发挥主导作用的空间吗?
闫涵:我不是故意这么想的。首先,我不太赞同“演员年纪大了演不了主角”这种说法。另外,我并不认为演配角就一定比演主角差,尤其是我们有时候要靠配角的精彩演绎来渲染主角。这些老演员有很多的表演经验和技巧。不管我拍不拍这部电影,他们也是整个电影行业演员中非常重要的骨干,是支撑整个电影行业的演员。所以不能说我是在给他们创造空间,更多的是因为我想表达一个老年题材,需要四个这样优秀的老艺术家来帮我完成。
澎湃新闻:就人生阅历而言,他们都比你更有发言权。他们给你带来新的灵感了吗?
闫涵:他们带给我最大的感受其实是在节目之外,让我对衰老和变老有了新的认识。有时候在现场看到他们的活力,觉得比我强。有时候我们总说很多年轻人好像每天都很压抑,而当我看到他们那么热爱生活,活得那么津津有味,每天的工作都充满活力,我很受鼓舞。突然觉得变老并不可怕。如果我能像他们四个一样变老,那将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。而且他们也不觉得自己老,在现场和我们小朋友交流也没有障碍。打破一些刻板印象对我来说可能是非常大的收获。
尤其是贾辉哥,我以为他可能是四位老师中最认真的,但恰恰相反,他是最积极的。其他老师也是如此。他们认识之后,大洪哥每天也是一副轻松的状态,可以和大家打成一片。
拍电影也是为了解答我自己的疑惑。
澎湃新闻:我们注意到在你的创作中,“滚蛋!肿瘤君,动物世界,我爱你!”都是漫画改编的电影作品吗?目前国内由漫画改编成电影的作品并不多。与传统的文学改编相比,它有哪些特殊性?
闫涵:我记得几年前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。当时我会回答这个问题,说漫画改编成电影,因为已经有画面和构图了,甚至还有分镜,改编成电影会很得心应手。但是今天再次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,我的回答正好相反。我改编我爱你!在这个过程中,我会努力忘记漫画里的画面。我在创作中只提取对我有用的素材,或者只过滤一些框架性的内容,其余的空间都是我的想象空间。我会努力摆脱漫画里的画面感,构图感,甚至动作感,我想摆脱。我脱胎于漫画,却想创作出完全不同于漫画,没有漫画质感的东西。而且以前拍漫画改编的作品,会刻意追求它的漫画感,这次是在摆脱它。我想去除漫画本身的影响。我只想把这个故事留在漫画里。
澎湃新闻:近年来有一种说法叫“哭片”,哭甚至会成为一种宣传策略。如何看待观众对于「哭」的情感诉求?
闫涵:哭或笑都很好。喜剧或戏剧。当人们用“哭电影”或者“哭”“搞笑”来形容一部电影的时候,我觉得这说明了一个问题,就是ta被感动了。哭和笑都是被感动的结果。观众去看电影,一定是为了这个目的。永远不会说我是带着目的看的电影,看完没反应吧?
但其实我在创作的时候,从来没有觉得它是在哭,是在搞笑。创作的时候我只考虑一点,在观众面前我是否被它感动。观众所谓的“哭点”是设计不出来的,也是无法提前铺设或捕捉的。我觉得我们的创作只能是真诚的,真心的,不要用太多所谓的技术。
而且我认为哭和笑都是减压的方式,甚至有科学证明哭比笑更减压。甚至在我们中医里面,有一种每天哭15分钟缓解肝郁的盲药。我们中国人有时就是太坚强了,不会让自己在某个时刻哭泣,这对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没有坏处。
澎湃新闻:这么多年来,你的很多作品,你监督的人生大事,都是关于生死相关的话题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特别关注这个话题?
闫涵: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深深地感受到了。从小就觉得自己和同学家人都很忌讳谈论死亡。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不要谈论死亡,不要接触死亡,认为死亡是不好的。这种想法一直是根深蒂固的东西,直到我上了大学。直到遇到熊顿的故事,我突然发现,她竟然可以如此坦然地用微笑面对死亡。她似乎为我打开了一扇窗。当时我就在想,我们为什么要害怕,为什么要避而不谈。
而且,在我看来,生死也是影片的终极关怀。我觉得没有什么比生死这个命题更适合拍电影或者拍文学作品了。所以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,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学会面对死亡。
澎湃新闻:你现在的人生观是怎样的?
闫涵:死亡是一种我们无法逃避的机制。当我们真正能面对的时候,我们才能更好的活在当下,珍惜现在的生活。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太快了,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有焦虑。他们每天都在担心自己的健康,是心脏不好还是血压高,但是去医院检查也没什么问题。这种表现的底层逻辑其实来自于对死亡的恐惧。大家都不是70岁80岁,但是为什么三四十岁就开始怕死了?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太大,每天作息不规律导致睡眠和休息不足。因为层层因素的叠加,他们慢慢开始想,我会不会猝死?对死亡的恐惧已经成为我身边经常发生的事情,所以我去拍这些题材。我有时自己也这样做,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回答我的疑问,给自己打一针强心剂。
澎湃新闻:你人生三部曲的第三部《让我们撼动太阳》怎么样了?未来导演创作有什么计划?
闫涵:我以前的作品是有计划的,但在一朵小红花之后我停止了计划,所以很多事情可能不会按计划进行。所以我现在更多的是一种回归最初创作的状态,任何能打动我的东西我都会拍。我不刻意追求一些探索,让自己去探索不同的类型,甚至说也许我没那么喜欢这个类型,只是出于好奇去探索,现在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我应该回到我自己的内心。如果我对这件事有感觉,哪怕是在打字重复自己,也没关系,因为我就是想表达这种感觉,所以就表达吧。至于我是在重复自己,还是在突破自己,还是在探索自己?都是观众来评判的。
《我们一起摇太阳》已经拍完了,上一届电影节开始前几天刚刚拍完。也许等我写完“我爱你”!“宣传,这将进入后期。
如果你觉得好,欢迎分享此网址给你的朋友。更多内容请关注《我爱你!》专区。